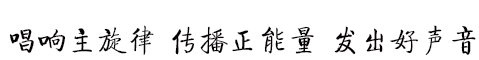□ 方维
与石达开部激战
1855年11月,湘军发起吉安战役。吉安位于江西省中部,是太平天国重要的战略基地,是阻止湖南清军进入江西的咽喉要地之一,此时,太平军石达开部几乎占领了江西全境。一天,杨秀清忽然调石达开返回天京,参与攻击“江南大营”。石达开回京前,留下岳父黄玉昆主持江西军务,节制各路兵马,与湘军对峙。湘军虽然发起反攻,但太平军士气高昂,作战勇猛,湘军屡战屡败。
围攻吉安,自然是湘军打头阵。湘军前后增兵2万余人,刘长佑、王錱、周凤山、曾国荃、普承尧、萧启江等主要将领全部参与战斗。开战之初,虽然取得了几次微小的胜利,但由于周凤山的麻痹大意、指挥无能,就算有普承尧等悍将的拼死作战,也难以挽回湘军失败的命运,致使大营两次被太平军烧毁。继而,湘军只得采取围城消耗战。后来,在黄玉昆的接应下,被围困在吉安城内的太平军突围而去,最后,黄玉昆也战死沙场。
清咸丰五年(1855年)七月,塔齐布因久攻九江不下,愤恨呕血而死。塔齐布病亡后,曾国藩把普承尧部拨给儒将罗泽南。
归入罗泽南麾下
罗泽南于清咸丰二年(1852年)以在籍生员的身份倡办团练,次年协助曾国藩编练湘军。罗泽南智勇双全,有曾国藩“左右手”之称,他率湘军转战江西、湖北、湖南三省,打了不少胜仗。罗泽南与塔齐布在指挥作战方面截然不同,罗泽南以谋著闻,塔齐布与勇著称,能先后跟随两大湘军名将作战是普承尧的福气。经过历次战斗的磨炼,普承尧从当初只懂冲锋陷阵的勇将转变为一名能排兵布阵的总兵。
罗泽南在整体战略布局中有自己的独到之处,在收复江西的战役中,他认为江西的军事部署不合理,就向曾国藩建议:“九江逼近江宁,而且向西牵制武昌,故太平军以全力争之……想要扼制九江,最好是从武昌而下,要想解武昌之围,最好从崇阳、通城而入。为今之计,应当以湖口水师、九江的军队截住太平军鄱阳湖的船,选能征善战的军队扫灭崇阳、通城的太平军以进入武昌,以武昌来扼制九江。那么东南的全局,就会有转机。”曾国藩将他的建议奏报朝廷,于是罗泽南得令,集合塔齐布旧将彭三元、普承尧等部人马,一共5000人,前往湖北围剿太平军。
湘军顺利占领了通城、夺取桂口要隘,进而攻克崇阳。太平军韦俊、石达开部合军2万余人从蒲圻进攻,被罗泽南部击败。在湘军将领胡林翼配合下,罗泽南率领普承尧等部趁大雾收复咸宁,使武昌以南再无太平军踪迹。接着,他与李续宾偷袭太平军十字街大营,抢占八步街口和塘角,保证了湘军粮路运输的顺畅。清咸丰六年(1856年)三月,长期闭门不出的武昌太平军突然开门出战,扑向湘军,罗泽南亲自督战。太平军援军接踵而来,湘军从洪山出动,与太平军激战。这时,一块弹片击中罗泽南的左额,他在将士的劝说下退回洪山,但仍然端坐在营外指挥作战。第二天,罗泽南在军中安然离世。
建德之耻
1856年7月,湘军水师将太平军浮桥烧断,对太平军后勤补给造成了不利影响。12月,曾国藩令刘腾鸿、吴坤修、普承尧率5000人往援,以其弟曾国华领其军。依次攻克咸宁、蒲圻、通城、新昌、上高,以达瑞州。刘腾鸿战城南,曾国华和普承尧战城西北,屡次打败太平军的反攻。水师斩断拦江铁链,武汉三镇江面太平军战船全被烧毁。待曾国藩大军到,便把整个武昌城合围起来,断了太平军的粮草接济。此时,武昌、汉阳太平军粮饷耗尽,决意突围。湘军乘胜追击,太平军54名将领被俘,伤亡兵士上万人,太平军不得不放弃武昌。
1856年的“天京事变”直接削弱了太平军内部的力量,太平天国名将杨辅清因奉命统兵驻守江西瑞州而得以幸存,于是驻军江西抚州,不敢回京。清咸丰七年(1857年),杨辅清部从安徽出江西彭泽、饶州、弋阳,进攻福建,连克光泽、邵武、建宁等郡县。九月,折回江西。十月,石达开从安庆入江西,杨辅清与之会合,再攻福建。清咸丰八年(1858年),杨辅清与石达开分道扬镳,复从福建浦城折回江西围攻建德,湘军总兵普承尧虽拼命抵抗,无奈太平军黄文金部自东流县攻建德,湘军溃败,丢失县城。曾国藩惊闻普承尧所守建德面临危机,急令沈宝成带亲兵回救建德。三日后收到凶信,建德已沦陷,事隔两天,紧邻建德的东流县也告失守。后来,太平军主力奉命西进,曾国藩才又率领亲兵营会合普承尧收复建德。
普承尧在湘军中一贯以勇著称,但其也有自身的不足,建德之战便成为其一生的耻辱。按曾国藩的评价就是“有勇无谋”。例如,清咸丰七年(1857年)二月,曾国藩父亲过世,按封建丁忧制度,要解职回家奔丧。曾国藩在奔丧期间也不忘江西军务,命其弟曾国荃率军到吉安,同时写信提醒他需要注意的事项,其中有一条就是专门针对普承尧的:“不要轻信普承尧,他是个浪得虚名之粗汉,打仗不动脑子,仅凭一股勇气冲阵,排兵布阵,毫无章法可言。” |